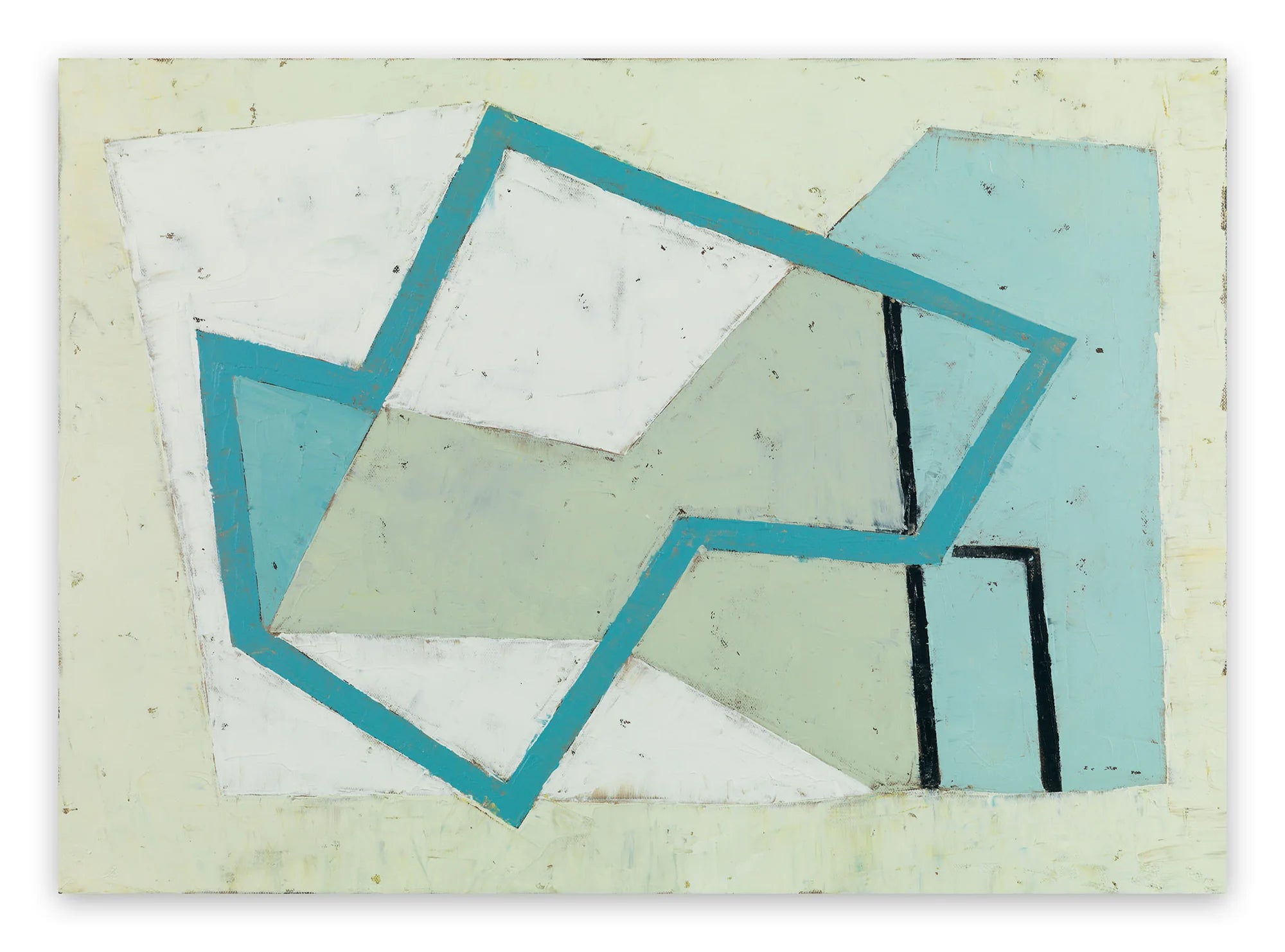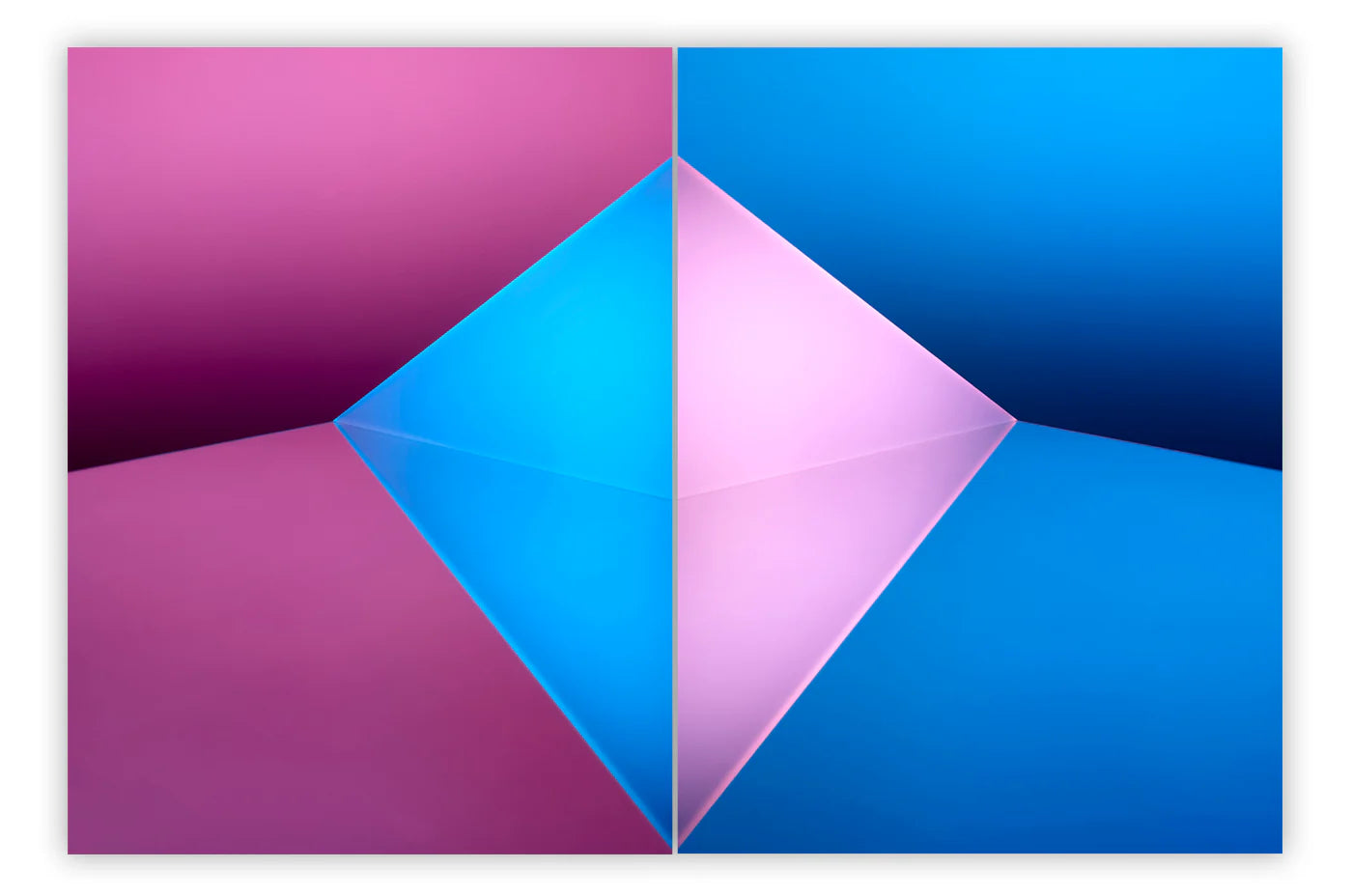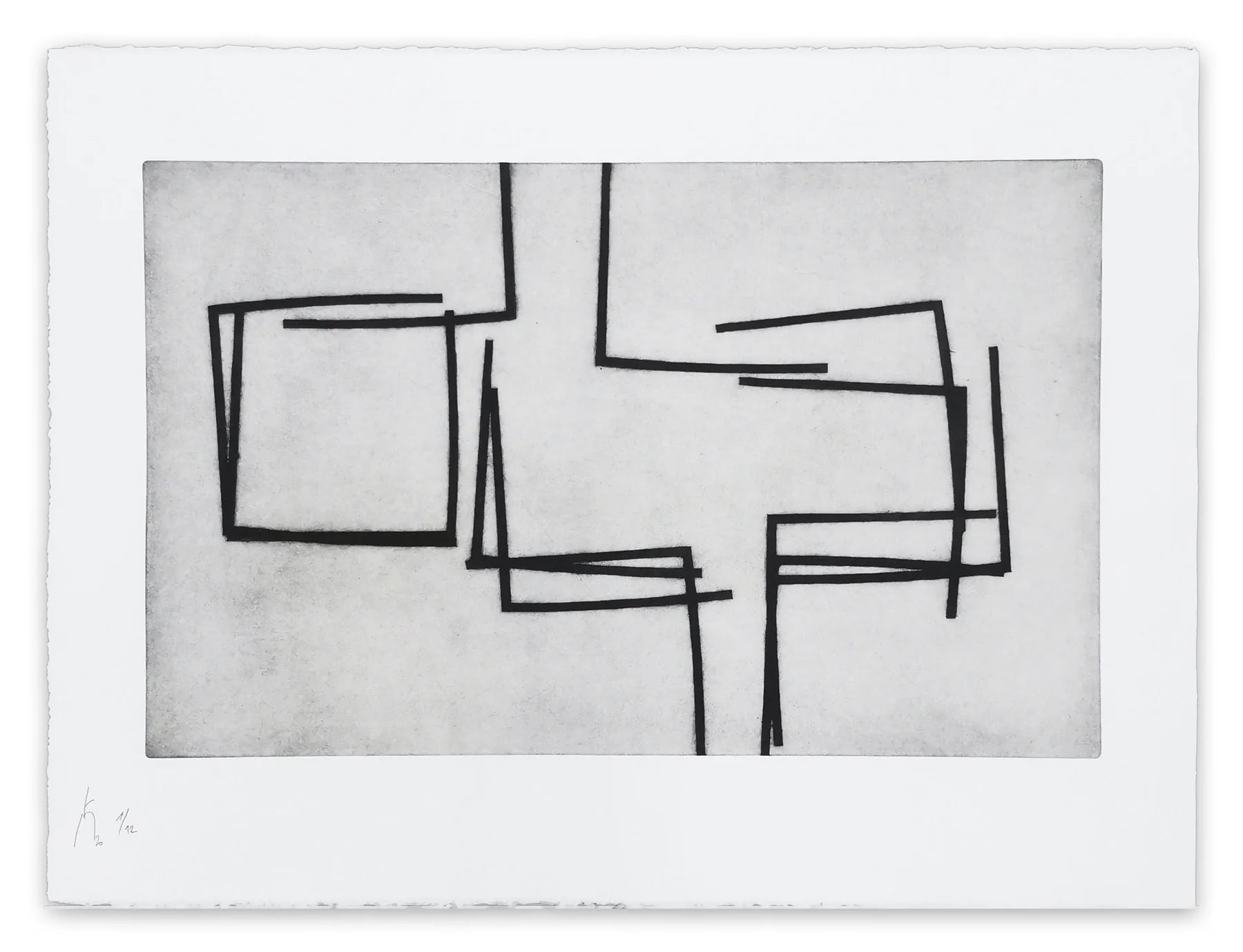《在巴黎的羅斯科:達娜·戈登的筆記與反思》
巴黎很冷。但它仍然擁有令人滿意的魅力,四周都是美麗。宏偉的馬克·羅斯科展覽在雪覆蓋的布洛涅森林新博物館,路易威登基金會,這是一座由弗蘭克·蓋瑞設計的華麗塑膠建築。它的餐廳叫做Frank。畫廊很不錯,畫作在非常昏暗的畫廊中以克制的聚光燈尊重地展示。一旦你的眼睛適應了,作品便在自身的能量中閃耀。
你首先會看到的房間裡展示了羅斯科1950年代的傑作。這些確實是傑作。在這些年裡,羅斯科建立了他持久的格式,通常由兩到三個柔和的矩形形狀一個疊在另一個上面,位於畫布邊緣的垂直矩形內,這個邊緣似乎幾乎無關緊要。在這件作品中,他使用了全色譜中最強烈的顏色組合。對我來說,這些作品是他最好的作品。它們展現了顏色最充分的表達。我發現它們很容易讓我凝視,吸引著我,並讓我想要看得更久更久。我看得越久,它們就越好。這個充滿如此多作品的大房間告訴我,繪畫,這些畫作,這位藝術家的畫作——這些薄薄的膜在脆弱的表面上——提供了世界所能提供的最深刻和最燦爛的體驗。在離開這個畫廊後,我回頭看,心中有了認識,對自己說:“他做到了。”
在那個房間之後,我下樓去看他的早期作品。首先是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中期的畫作。這些作品通常是緊湊、無空氣、幾乎無色的城市和少數人的形象。然後我們看到了一些受超現實主義影響的抽象畫作。這些作品顯示出稍微的開放,但大多數是細長的、線性的,並且有所保留。
然後就好像羅斯科在1947年服用了迷幻藥。那些自由的「多重形式」——柔和漂浮的色彩形狀突然出現,開放而自由,閃閃發光。這些是我們所熟知的標誌性「馬克·羅斯科」畫作的清晰序幕,將在1950年代到來。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是,他看到了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的博納爾展覽。在1947年至1951年這段奇蹟般的時期背景下,紐約的繪畫發明了一種新的抽象形式,一種新的繪畫(不久將被稱為抽象表現主義),並伴隨著它的傑作,博納爾的畫作催化了羅斯科的偉大突破。

馬克·羅斯科 - 黑色與栗色,1958年。油畫,畫布。266.7 x 365.7 公分。倫敦泰特美術館。由藝術家通過美國藝術基金會贈送,1969年。© 1998 凱特·羅斯科·普里澤爾與克里斯托弗·羅斯科 - Adagp,巴黎,2023
另一個催化劑浮現在我腦海中——也許是一個過於遙遠的思維橋樑——就是懸掛在垂直畫布上的顏色和光線矩形的格式大約是4比3的長寬比,這是1920年代到1950年代大多數電影影像的形狀。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許多此類電影的一個新而引人注目的特質是強烈的技術彩色反射在螢幕上。看著羅斯科的矩形讓我想起了當你仔細觀看這些電影時所看到的旋轉顏色顆粒。
在1950年代的房間之後,是1960年代的房間。這在某種程度上是驚人的。整體顏色較暗,但仍然強烈。羅斯科曾說過,他希望他的畫作能夠成為戲劇性的體驗,而不是抽象的裝飾。這種強調在這裡變得明顯。在1950年代的作品中,明亮的顏色無疑是戲劇性的,但觀眾的體驗更多的是沉浸在顏色本身的愉悅和深度中。這無疑是一種體驗,並且戲劇性強烈,但並不是以戲劇為主導。在1960年代的作品中,顏色的黑暗和形狀的強調性擺放——例如,頂部非常明亮,其他部分則較暗——顯示出通過視覺手段表達戲劇的意圖。
接下來是一個房間,裡面展示了為新西格拉姆摩天大樓的四季餐廳製作的壁畫面板,該摩天大樓由米斯·范·德·羅設計。羅斯科是由菲利普 Johnson 委託的,約翰遜是1960年代的建築師和藝術界的風雲人物。羅斯科意識到這些畫作將裝飾一個喧鬧的高檔餐廳,主要由企業高管光顧,於是他在完成畫作後拒絕釋出它們。當你現在看到它們安裝在為它們而設的房間裡時,你會明白他為什麼這麼做。這些畫作幾乎摒棄了顏色,由大型、奇特、極具戲劇性的形狀和黑暗組成,其氛圍並不適合用來吃晚餐。

馬克·羅斯科 - No. 14, 1960。油畫。290.83 cm x 268.29 cm。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 - 海倫·克羅克·羅素基金購買。© 1998 凱特·羅斯科·普里澤爾與克里斯托弗·羅斯科 - Adagp, 巴黎, 2023
接下來,幾乎是最後的高潮,或反高潮,是羅斯科在1960年代末的黑色和灰色丙烯畫。對我來說,這些作品體現了他從1947年到1960年代末的成功突破的深刻感傷,逐漸下降至他最後幾年抑鬱的無情荒涼。這些畫作大致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面是黑色,下面是淺灰色。表面筆觸粗糙,但遠不如之前那樣細膩。丙烯顏料是平坦的,只是惰性地反射光線(或者像黑色一樣吸收光線而不反射回來),它不會像他之前的油畫那樣吸收並折射光線回來。它不會吸引你。這是一個塑料屏障,將你隔絕在外。除了其中一幅,所有這些畫作的邊緣都有一條約3/4英寸寬的白色線條,顯然是遮蔽膠帶的寬度。還有一幅可以看到用來保持邊緣銳利的膠帶殘留物。這些邊界強調了畫作內部的邊緣,並幫助保持平面形狀的不可穿透性。的確,人們通常可以想像黑色是深空,但在這裡忽視了顏料的效果。有些人說這些畫作是羅斯科對1960年代中後期的極簡主義的回應。也許是,也許不是。無論如何,它們幾乎與他之前的絢麗色彩作品毫無共同之處,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當時眾所周知,羅斯科正遭受日益嚴重的抑鬱,這正如我們所知,最終導致了他在1970年的自殺。
我曾在1968-69年遇見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一次。我當時為他的朋友、雕塑家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工作,負責接送馬克和他的家人,從他位於東69街的工作室開車帶他們去新澤西的托尼和簡·史密斯(Jane Smith)家吃晚餐。我和一位朋友被邀請留下來共進晚餐,然後再把羅斯科一家送回紐約。斯塔莫斯(Stamos)也是一位客人。托尼的一幅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作品掛在晚餐桌後面的牆上。我不記得具體的對話,遺憾的是,除了沒有關於藝術的深刻討論,只是正常的閒聊,而羅斯科的貢獻不多(我也是)。我還記得羅斯科給我的感覺像是被一層陰霾籠罩著,像是一個縮小的黑洞,充滿了抑鬱。就像他晚期的黑色和灰色畫作一樣,他沒有散發出任何能量,似乎在吸收光線,幾乎不反射光。也許這對當時的年輕畫家來說尤其引人注目,因為這與羅斯科最近過去的偉大作品所投射出的細膩旋轉的光能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知道他的同時代人也有類似的感受,無奈地對此無話可說。
達娜·戈登是一位駐紐約的美國藝術家。他對藝術的寫作曾出現在《華爾街日報》、《新標準》、《畫家桌》、《紐約太陽報》、《評論雜誌》和《耶路撒冷郵報》。